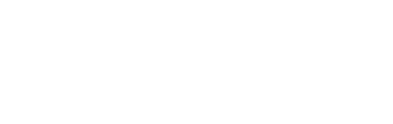其人其事
總有一個人,在你生命的畫布上,留下一抹虹,或一整面絢爛又沉著的色彩。

甕仔雞 周玓
甕仔雞誘人的香氣伴隨著特製的胡椒粉味瀰漫在空氣中,碰撞出使人垂涎欲滴的火花。二姨將餐盤小心地放在桌上,說雞身中還塞了不少藥膳是給我補身體的。我看著她疲憊的臉上露出慈愛的笑,鼻頭竟不由自主的發酸。
唸幼稚園前我一直住在成天都有甕仔雞飄香的二姨家。即使幼年的記憶早已伴隨著稚氣與青澀在歲月中漸次凋零,但在二姨家的那段日子大概是一幅色調溫暖的油畫,始終懸在我回憶的牆上,就算隔著不短的距離也能一眼望見那些明亮的色塊,略為模糊、但絲毫不減美好。我永遠記得二姨長年做家事的手替我搓洗頭髮的觸感,粗糙又無比溫柔;記得年幼的自己睡在表姊房間時總會踢開被子,二姨便會在半夜偷偷把我連人帶被抱進主臥室,摟著被包成一團的我直至天明。記得二姨總會把年幼的我帶進店裡的廚房,烘甕仔雞給我吃,告訴我這一整盤都是加了中藥材的,對身體很好,成本太高就不拿出去賣了,只給我吃。我永遠記著二姨講這番話的情景,眼裡有溫柔的光閃爍,竟比甕仔雞迷人的香味更吸引年幼的我。
小學五年級的寒假,二姨全家帶著我出門去玩,回程的路上我坐在車裡,正被車身搖晃的節奏弄得昏昏欲睡時,二姨忽然伸手捏了捏我的臂膀,略帶嘆息地說:「你長得這麼快,每次買新衣服想給你穿,過半年回來就穿不下了,好可惜。」我笑著回應她說自己還在發育期,長得快是應該的呀!轉過頭面對車窗時卻忍不住淚流滿面。平時我住臺北,二姨在臺南,原以為用電話聯絡就能彌補的空白卻透過平平淡淡的一句話,帶著半個臺灣那麼遠的思念直直衝進心窩。我想,二姨大概是第一個教會我「想念」是什麼滋味的人吧。直到現在,每每碰上挫折、覺得沮喪的時候,我都會告訴自己:撐下去,再過幾個月就可以回臺南吃二姨烘的甕仔雞了。那熟悉的香味,竟成了我成長過程中緊緊攀附的繩索。繁事人群散亂之際,我不知為何回頭,二姨就站在那裡。安靜地溫柔的不變的,我相信那是在等待自己,一定是在等待自己。
我想告訴二姨我不要長大了,我想一直陪著她就像以前那樣,想告訴她臺南的生活太過美好而我非常想念被甕仔雞香味環繞的日子,非常想念她。但最後我只是站起身,走到廚房去幫忙。跟隨著她的背影。

童年追求的笑容 袁子淇
「淇淇啊……」位於客廳波斯地毯的中央,外公喚著我。不同於平日的有條不紊,他身著的是細藍色條紋的鬆垮睡衣,帶著一絲憂鬱。
每周六晚上,是個熱鬧的家庭團聚日。外婆炒起拿手好菜、姑姑阿姨備著餐具,鍋碗瓢盆的敲響此起彼落地在孩童的嬉笑間響起。「開飯囉!」一聲令下,小孩子們總頂著唱空城的肚皮奔向桌筵,「沒禮貌!阿公還沒來!不能先吃!」阿姨瞬間打了一下那雙躁動不安的小手,如此喝斥道。背後傳來沉重而有規律的步伐,身高高人一等的外公此時更令人敬畏,仰頭望向他的孩子們只能如寒蟬般不發一語,待外公開動後才怯怯地夾菜,開始一段靜默的晚餐。
這就是我的半個童年──皇族般的生活。奔跑在偌大的日式房間,典雅高貴的油畫懸在走廊的一端,搭配合宜的花團錦簇,時不時點亮我的餘光。但使我佇足的並非美麗的花兒們,而是在我面前、蹙起眉頭的外公。「淇淇,別像男生到處跑,要有女生的樣子。」和那時我興奮展示自製竹手槍時,他說了一樣的話。我也許是個太活潑的小公主吧!外公每次看到我總面露難色。不同於我其他皇兄皇姐們、不同於那些令家族沾光的輝煌成績,沒什麼才能的我,只能看著外公以心滿意足的笑靨溫柔輕撫其他同齡的孩子。
不知該說妒嫉?或只是「不慕榮利」?我不曾試圖爭奪皇太子的寶座──外公最寵愛的小孩。「大家都太優秀了,我知道。」讓一個不滿十歲的小孩知道自己比不過數學奧林匹亞代表選手、北一女中畢業台大經濟系、跳級讀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資優生……這些非凡的表哥姐弟妹們,也是個頗殘酷的事。那年慶祝七五大壽,在其他孩子們分享自己璀璨的成績後,我抿著沒自信的下唇,以顫抖的雙手遞出自己的卡片。不敢抬起的臉龐,在一雙粗糙的手接下卡片、撫摸自己的頭頂時,不可置信地看見一份真誠的笑容。平時只能看到深鎖眉頭和無奈嘴角的容顏,第一次,因為我而露出真摯的微笑。
「淇淇啊,記得每年你都會畫一張卡片,在生日時給我……」緩慢而低沉的嗓音,不如之前的有力,但仍平穩踏實。外公勾起一樣和藹的笑容,如觸著嬌嫩的花瓣般,輕拍我的手背。這是我最後一次聽到外公喚我「淇淇」。
放下一張繪有黑白素描的卡片,也許,正因自己仍保有一絲勇氣,伸出雙手、送出我的真心,才能不被嚴肅的日式教育擊潰幼小的心靈。謝謝外公的嚴厲,讓我有不同一般人的氣度、家教;謝謝外公的慈愛,在我逐步長大後才理解溫柔。「謝謝阿公,用微笑告訴我,你是愛我的。」闔掌、離去,香上的一縷煙,攜著字句,在外公的笑容前,輕輕散去。

公事包 高語彤
父親那只黑色的公事包已用了很多年。上頭夾了一個燕尾夾,取代損壞拉鍊的功能;部分皮層開始龜裂,黑色的小皮屑如螞蟻般攀附背包裡的物品,但父親只是輕輕地拍掉。母親曾精挑一只氣派不凡的公事包要送給父親,然而父親悄然拒絕。他認為背包合用就好,品牌只是一張奢侈虛幻的標籤。他就是這麼一個樸厚的人。
年輕時的爺爺是個極不負責任的父親,好賭成性,原本該花在家庭照顧的鈔票成了一張張彩票,在那物資貧乏的年代,父親家中經濟更是雪上加霜。父親高中時,和爺爺大吵一架後便無心讀書,一畢業便四處流浪,到處打工。他在烈日下搬過磚頭,在化工廠裡聞過臭不可當的藥劑,也曾在飯店當服務生。當時父親望著那些西裝筆挺、手提公事包的富人氣宇軒昂地走進飯店享樂,便默默立下有一天要和那些人一樣到飯店享受的夢想。
皇天不負苦心人,父親的夢想實現了。憑著克勤克儉、不畏勞苦的毅力,他考上公務員高考,有了穩定的收入,終於能到飯店好好享用一餐。唯一不同的是,他手中握的不是公事包,而是他孩子的手。
父親是個含蓄木訥的人,他不會說冠冕堂皇的客套話,不會勾心鬥角的為官之道,卻對他的屬下十分照顧。也因此,出門前扁瘦的公事包,回家時竟鼓胖起來。裡頭裝的,有時是他的同事自家種植的水果,有時是他的屬下出國買的當地特產,有時還有同事親手做的牛軋糖。同事們有什麼好東西總不忘留給父親一份,或許是要表達對平時父親照顧的感謝吧!然而,長官們卻不認得他,在父親工作的漫長歲月裡,他的名字不曾在升官名單上出席。公布升官人員時,父親不免顯得有些失落,但想到他深愛的家人,隔天又能再見到父親容光煥發背著公事包的敦厚背影。
出生成長在不虞匱乏的環境中,我恐怕一輩子都難以達到像父親那樣勤儉的境界。不過,父親簡樸的基因終究是遺傳進我的體內了。我最喜愛的外套從小五穿到現在,雖然袖口早已鬆垮,色澤也由深藍褪成了蒙上一層滄桑的灰藍,卻沒有別件外套能取代它穿在身上的舒適自在。
印象中,父親的公事包看起來扁扁的,除了便當盒、幾份文件報告和當天的報紙之外,似乎沒有什麼特別。
直到有一天,在我無意間自背包中拿出報紙時,一張照片輕輕地滑落,而照片中的主角是我。原來父親一直帶著我的照片去工作,原來,父親的公事包其實裝滿了東西,那東西,是他對我無盡的愛。

小提琴 張傳瑀
一曲終了,掌聲響起,他微笑著,向台下的人以及評委們深深鞠躬。夢想與渴望,體驗與嘗試,我看見了他對這把小提琴的熱情和對演奏的渴望與執著。我們年齡相仿,但在他身上似乎有著不凡的光芒,燃起了我對小提琴的渴望。八年前,一個小男孩以一首莫札特《小夜曲》感動了小女孩;八年後,小女孩以一首莫札特《小夜曲》感動了全世界。
「四弦音調沈悶,就像等不到王子的仙度瑞拉;三弦音調溫和,就像夏天溫暖的風;二弦音調歡快,像蝴蝶在花上跳舞;一弦音調清脆,如麻雀在枝頭上唱歌。」童言童語間,他比手畫腳跟我形容著印象中音符和弦帶給他的感受。那一年我們才二年級,他是我的青梅竹馬,在我心中,他的魅力任貝多芬、舒伯特都比不上。那一年夏天,我開始學小提琴,模糊的記憶中,也許是琴聲打動了我,又或許是單純想和他一樣,在弓與弦間發現快樂。
我們第一次的演出是校園音樂會,第一次那麼頻繁練習,和他朝夕相處。在練習過程中,我們學習,我們成長,我們鬥嘴,我們合好。他教我如何數拍、抖音、十六分音符;也教我閉著眼睛,聆聽約翰史特勞斯奏鳴曲的感動。跟著音樂老師學小提琴,技巧和樂理我已爐火純青;跟著他學,體會和享受我才漸漸明白。我懂了所謂四弦的道理,在我生命中,我和小提琴的緣分,建立在我和他的相識,我和莫札特《小夜曲》的邂逅。中途我曾失落、挫敗,但我總是想起他說的一字一句。他送我的那片自己錄的CD,裡頭的歌是他的最愛和我們的回憶。我們第一次演出的小步舞曲也成了往後日子裡練琴時第一首拉的曲子。透過小步舞曲,我告訴自己,我愛小提琴。拉著拉著,我闔上雙眸,沿著我們一起走出的那條音樂小徑,在五線譜上彈跳自如,又拾起八歲那年對小提琴真摯的感動……
多年來的砥礪已使我了解原泉滾滾,盈科而後進的道理,讓我成長茁壯。驀然回首,撫摸著小提琴,那份悸動在我心頭蕩漾。不再彷徨,不再迷惘,放著他送我的那片CD轉啊轉,一顆顆音符譜出的是我們的回憶。再次闔上雙眼,小女孩拿著琴,用一首莫札特《小夜曲》感動了我……。

生活扣環 藍宜庭
記憶的深罈一旦翻了,四竄的濃淡酸苦便鑽進全身細胞,刺得難耐。
家庭於我自出生以來,便是溶不開的混合液,且溶合得愈發均勻,說家人對小孩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是墨汁靜悄悄流淌填滿模版,然後複印出相似的一代又一代。記得我小時候對爸爸的印象是十全十美,彷彿什麼都問不倒他,每每困擾的拿著問號滿滿的話語,經由他,那些問號都成了肯定句,懵懂的我,對於這樣的學問是崇拜的。
背影也是一張烙印在腦中的泛黃影像。感覺跟爸爸的互動,從時間軸看來不是織著那麼密麻,電腦桌前閃亮明滅的光映著端坐的身子,這樣的畫面存留了好一段年歲。某次的父親節卡片,我畫的就是背影,回想起總覺得那是一種孤寂。時光翻滾了一圈又一圈,望著的背影變成了我的,可我不知道是從小看慣了還是成長壓著我向前,必須背對,然後想受一個人。也許我沒有習慣孤獨,不像爸爸能圍個自己的世界,獨自,是爸爸的個性。
威嚴是一道薄而堅實的牆面。我是個怕擦傷碰撞的易碎品,承受不了顛簸。忘了為什麼,但有力的嗓音把我的眼淚震碎了一地,被罵是如此難受,但是很久以前了。漸漸我知道他就是說話太直、容易有脾氣,但本意通常是關心,包裹著好意的帶刺言語,雖有些畏懼,卻也不那麼令人錯愕難耐。聽媽媽說,我也有他的影子,不知是否兒女就是如此?在無意識的引導下緩緩成形成極類似的模型。
爸爸的一切是那樣熟悉,仔細端倪又有丁點陌生,他不會把想法一股腦兒掏出來攤平,我和媽媽多少還是會懂。記憶的氣味發酵了吧!把罈子扶正,繼續注入更多香醇。